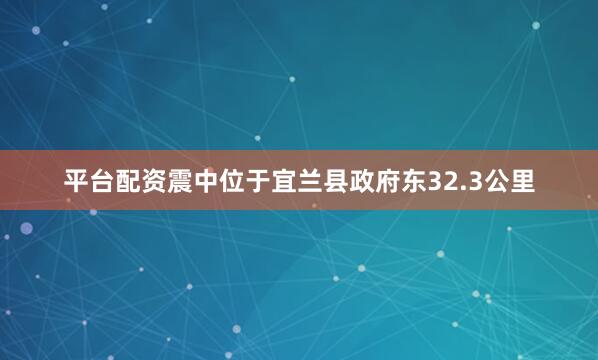股票杠杆公司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部分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于重庆与美国飞虎队成员进行了会面。

▲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与飞虎队成员霍华德·海曼(左)及翻译龚澎(右)一同留下珍贵合影。
中国大学生与美飞虎队
(节选)
作者|张彦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节节败退,以至将政府迁至西南后方的重庆。当时,中国几乎无空军可言,日本飞机则集中对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伤亡惨重。在此期间,除了苏联曾以少量飞机支援中国以外,真正向中国伸出援手的是美国。
当时,美国尚未对日本宣战,因此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的名称,派遣了约300名空地勤人员及100架D-40C型战机至中国。这些勇士和飞机,日后成为了声名显赫的象征。陈纳德将军为首的“飞虎队在首战之中,他们便击落了十架敌机,有效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1年,随着美国对日宣战,那支英勇的飞虎队亦随之改编,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部分。第十四航空队自1943年起,飞虎队战绩斐然,总计击毁敌机2600余架,摧毁或重创舰艇44艘,日军官兵伤亡逾6万人。然而,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2500多名美国飞行员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牺牲。
书店巧遇
1944年春的一个周末,联大中文系的学生,亦担任中共联大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时称马千禾者,正漫步于南屏街头的书店之中。忽有两名美国士兵步入店内,左翻右找,似乎在寻觅着什么,却最终一无所获。他们注意到马识途手中正捧着一本英文版的《苏联文学》杂志,不禁喜形于色,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其中一位名叫——迪克,一个叫莫里斯他们均为飞虎队成员,正寻觅有关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相关书籍。其嗓音洪亮,言谈间毫无拘束。
老马听闻此言,心中难免焦虑,四处张望,唯恐特务窃听,于是低声告知他们此地并无此类书籍,即便有也是中文版本。“你们想探寻些什么?或许我能提供帮助。”两位美国士兵听闻,喜形于色。老马立刻带他们至附近的茶馆,开始畅所欲言。具备敏锐洞察力的马识途看出,这两位美国人的确渴望了解中国,并无其他企图,但苦于找不到途径,加之语言不通。他自觉有责任提供援助,一口答应为他们介绍几位精通英语的中国大学生。
天意使然,无独有偶。不久前,在昆明圣公会的主教主持的一场社交聚会上,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出席了活动。李储文结识了两名年轻美国兵。贝尔和海曼怀着对真实中国的深切向往,他们在交谈中流露出明显的进步理念,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态表现出极大的关切。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透露,在美军军营中,有着与他们相似心境的人并非少数。增进国际青年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本是青年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李先生立刻表示愿意伸出援手,决心努力实现他们的愿望。
云南曾是地方军阀统治。龙云的天下,与蒋介石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历来存在着既尖锐又微妙的矛盾。为推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正积极推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涵盖上层及国际层面。马、李两位渠道提出的这一特殊需求,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一个以马、李为中心的无形小组应运而生,致力于开展国际友谊工作,而参与这项活动的,除了马、李和我(张彦)之外,还包括几位英文水平较高的联大同学。许乃迥、周锦荪、涂光炽、何功楷、吴明在等待十人的队伍中,我始终坚守,是其中坚定的守候者之一。而美方参与者的行列中,继上述四位之后,也陆续汇聚了近十位同仁。杰克·爱德尔曼、耶尔·佛曼、尤金·莱西等。
自那以后,每隔大约两周,我们便相聚一堂,参与者人数各异。或是在李储文在青年会学生服务处的主持下,我们或在绿意盎然的公园草地上,或在五百里滇池的碧波荡漾中乘船漫游。我们一边品尝着美味的中国饺子,一边享受着开罐头的美式野餐,欢声笑语,畅快无拘。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热烈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我们分享着中国的时局动态,他们则讲述着美国的见闻,双方都感受到了新鲜感,彼此深受启发。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不禁感叹,若能早点相识,该有多好。

▲这幅照片摄于1944年,地点位于昆明的大观楼。画面中,联大的学子们与美国的飞虎队员一同定格了历史。在照片的后排左侧,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本文的作者。
相见恨晚
一边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边是挥霍无度的权贵,更有甚者,竟利用美援物资谋取私利。面对这一幕幕,他们感到极度沮丧,迫切地想要弄清楚这背后的原因。
对于我们这些勤奋学习、心怀天下的中国大学生而言,与这些美国青年的频繁交流,宛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不久,我们的热烈讨论便演变成了相互支持。鉴于当时昆明街头美军众多,每当联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总会同时分发英文宣传材料。这些英文传单,往往都经过美国人的精心润色。有时,甚至会有他们驾驶吉普车沿途为游行队伍拍照。我们与这些美国士兵的友好合作,更是发展到了他们邀请中国大学生进入美军军营进行演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夏夜。贝尔和海曼开了一辆卡车把李储文我们一行人,连同另一位联合国大学的校友,被载往昆明东郊的第十四航空队军营。那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已座无虚席,满载着数十位美军将士,热切期盼着中国大学生的到来,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我们踏入会议室的那一刻,立刻被热烈的掌声所包围。贝尔在致辞之初,我特别提及了我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紧接着宣布今晚将由我为大家揭开“中国解放区”的神秘面纱,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我站起身来,准备发表讲话之际,一位手持相机的美国军官缓步走近。他的政治阅历,相较于我们众人,显然更为丰富。李储文急忙上前制止了他的拍摄,我婉转地拒绝道:“请您见谅,他十分腼腆,并不愿意接受他人的镜头。”事后我才领悟,这实乃一种巧妙地避免招致政治麻烦的策略。
当晚发表演讲的学生身份为何?幸运的是,除了少数人外,我们与美军交流均使用英文名,难以追溯,此事最终无果而终。
然而,我们的美国友人却因此遭遇了不幸,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在部队邮局任职的知己暗中透露:“上级已下令,你们今后的所有信件都必须接受三道关卡的安全检查!”尽管如此,这些美国友人们并未因此感到畏惧。
1944年冬日,尽管日本侵略者的败势已显,却仍对中国西南地区发起猛烈攻势,企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贵阳形势危急,昆明亦深受影响。美国友人向我们透露,若日寇真的进攻,他们的空军将转移阵地,并询问我们的应对策略。我们回应,或许会效仿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前往云南农村进行游击战。听闻此言,他们激动不已,并表示愿意与我们并肩作战,甚至在技术层面上贡献力量。他们的态度庄重而认真,毫无戏谑之意。
1974年,纽约的迪克·帕斯特于《中国与我们》这一份美中友协的出版物中,曾如此追忆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鉴于对中国友人安全的深切关怀,我们火速将日本可能派遣伞兵突袭昆明的消息告知他们。我们未曾料想,他们对我们的关注,远超我们对其的挂念。就在次日深夜三点,我正沉睡于营房之中,突然被一阵摇晃惊醒。定睛一看,竟是——”张彦他透露,他们曾就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展开过讨论,并紧急派遣他骑自行车连夜赶来通知我们。会议作出决定,一旦袭击发生,便邀请我们几位美国人参与他们的政治行动,并承诺将保障我们的安全转移。尽管袭击最终并未成真,但那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不仅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团结友好的生动象征,更是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这一时刻,我们的美国友人已对中国局势有了深刻洞察。与我国同胞一样,他们敏锐地察觉,中国上空正弥漫着内战的乌云。
见毛泽东
此刻,我们的众多美国友人,怀揣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以及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深切关切,纷纷选择退役归国。在踏上归途之前,贝尔、海曼和爱德尔曼他们不遗余力地渴望能亲自向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代表阐述己见。在得到我们的引荐后,三人在归国途中特地抵达重庆,一同拜访了中共在当地的办事处。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前来接见他们的,竟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周恩来不仅是那样地充满热情与亲切,以至于他们感到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尽情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早已听闻他们的名声,如今亲身体验,果然名不虚传。毛泽东烟瘾难耐,他们便将几支从军中获得的香烟留作纪念,恳请周恩来代为转交。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个个洋溢着满足与喜悦,夙愿终于得偿。
他们未曾料想,数日之后,竟意外接到了一则通知:毛泽东主席盛情邀他们共赴晚宴。听闻此言,三人无不喜出望外。他们反复揣摩,这个邀请背后究竟蕴藏着何等深远的含义。四十年后,贝尔回忆当时情况:
我们满怀激动,热切期盼着那场晚宴。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伟人,终日投身于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却愿意特意抽空与三位普通美国士兵相见。这源于在他心中,中美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分量非凡。
那午后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如绘。海曼、爱德尔曼与我,急匆匆地穿梭于狭窄的巷道,朝着那座灰蒙蒙的宅邸迈进,踏上石阶。我们在楼下的一间屋内耐心等待,门上悬挂着由竹条编织而成的帘幕。不多时,帘幕缓缓拉开,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们面前,身着军装,面带微笑,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众人围坐在宽敞的大圆桌旁,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专注地倾听我们的每一句言语。他询问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关切地了解我们的家庭背景,并询问我们对战后生活的规划。尽管他不懂英语,但在聆听中文翻译时,目光始终紧随我们。通过翻译,我们畅谈了战争的意义、世界和平的珍贵以及中美友谊的深厚。席间,他多次举杯,为我们祝福。他郑重地要求我们,回国后,要将在中国亲眼目睹的一切如实告知美国人。他坚定地预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恒久长存。”
对那些赠予他的香烟,毛泽东在表示感谢之余,幽默地对他们说道:“你们真够大方啊,你们的大使...”赫尔利来延安仅抽了一支烟。
杰克·爱德尔曼在回忆录中,作者如此描述:“面对这位伟大的人物,我不禁感到一丝敬畏。他的身材高出大多数中国同胞,身上流露出一种威武的大将风范。他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对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数年前,有人曾向我提及,在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几段话多少涉及到了我们这几位美国士兵:‘我在重庆期间,深切地感受到广大民众对我们的热烈支持,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将希望寄托在了我们这一边。’”我再次目睹了众多外国友人的身影,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同胞,他们对我们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因而,我们已然略微涉猎了史上最为卓越的革命之一。
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三位美国士兵,这一幕成为了历史上一道璀璨的风景。在红岩村,毛主席与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见题图)它已化作中美人民友谊的永恒象征,永久地陈列在中国博物馆的展馆中,深植于民众的心田。
历史剧变
自那之后,历史,尤其是我国的历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美国政府所扶持的蒋介石政权,终究被人民推翻,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运而生。然而,美国政府仍旧对铁一般的事实视而不见,继续采取威胁、封锁、打击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试图将这一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中美关系由此步入了一个全面对抗的历史时期。我们与我们的美国朋友之间的交往,自然而然地中断了,并且长达三十年之久。
在这风霜雨雪交织的三十年间,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美两国均遭遇了政治动荡,我国与美国的朋友们同样未能置身事外。
1950年代,美国笼罩在“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进步力量普遍遭受重创。我们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磨难,有人被列入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有人遭受了监视,有人求职之路步履维艰。他们的“罪名”仅仅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与毛泽东及中国朋友们的合影,自然成为了所谓的“罪证”。他们不得不将这些珍贵的照片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地下,以至于相纸至今仍保留着那阴湿的黄色水迹。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的十年里,那些被视为“四人帮”眼中与美国有过接触的我们,被视为必须被推翻的对象,我们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被安在我们头上的指控,从“勾结外国”到“国际间谍”,各式各样,荒谬至极。然而,我们内心始终保持着清醒,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又何罪之有?
寻根之旅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新中国非但未曾被压制,反而在岁月的洗礼中日益强盛,朋友遍布四海。至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他乘坐专属的空军一号专机,莅临北京,展开了旨在“破冰”的访问之旅。周恩来经过深入谈判,双方共同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上海公报》,旨在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自此,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自那时起,我们的美国友人便踏上了他们的“寻根之旅”。恰逢尼克松总统访问我国的同年,迪克·帕斯特战后首次重返中国国土,心中充满了与昔日中国友人的重逢期待。然而,现实却让他的心情由期待转为失望。毕竟,自那以来我们已失去联络近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他们仅存我们的英文名和往昔照片,并无具体地址,我们又怎能寻觅?况且,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些人都曾是“文革”期间的“审查对象”,其中一些人甚至被送去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即便他真的找到我们,我们又如何能被允许接待他呢?
迪克尽管在老友间感慨万分地传递了这个消息,他却并未就此放弃希望。不久后,他在一份刊物上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年代中美友谊的传奇》,首次揭示了美国士兵与中国大学生在动荡岁月中所结下的特殊情谊。刊出当年昆明合影偶然间,这本杂志落入了我的手中。幸运的是,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些美国朋友的踪迹。然而,在那个艰难时期,我唯有将内心的喜悦与激动深埋心底,别无他法。

▲1944年,美国士兵与我国友人于昆明留下珍贵合影
在1976年的炎炎夏日,美国友人再次踏上了“寻根之旅”。彼时,“文化大革命”虽渐行渐远,但其余波仍余音绕梁。以贝尔与海曼及其家人为核心的“美国二战退伍军人访华代表团”满怀热情,重返这片久违的中华大地。贝尔与海曼紧握着那些满是往昔影像的相册,仿佛朝圣者般重返昆明、重庆等地……他们走到哪里,便询问到哪里,渴望找到那些深藏心底的中国老友。然而,一个个美好的愿望却最终化为泡影。
直至踏上访华的最后一程,我终于在上海寻得那位当年唯一以中文姓氏铭记的历史人物。李储文的关怀,他得以在政治环境尚未完全宽松的情况下,有幸接待了来自国外的客人。作为当时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精神领袖,他的身份特殊,自然无法轻易与外国访客接触。然而,得益于负责旅游事务的领导们的特别关照,他得以在适当的时机,迎来了这些尊贵的来宾。岳岱衡思想解放,大胆批准特殊会见。李储文与夫人章润瑗在和平饭店设宴款待。
任何一位心智健全之人,无不预见到这场老友的重聚将何其令人振奋。双方心中满怀憧憬,热切期盼着这一历史性瞬间的降临。然而,那个时刻,笼罩在每个中国人思维与行为之上的“政治氛围”,却将一切美好扭曲。在会面之际,李储文尽管内心汹涌澎湃,夫妇俩却不得不竭力克制情绪,仅以寻常的应酬之谈敷衍,不敢多言一句。海曼夫妇俩特意将已长大成人的女儿引至主人面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对她说:“正是这些中国朋友,塑造了你父亲的人生轨迹!”此刻,李储文夫妇内心澎湃,千言万语似乎都在脑中汹涌,但他们并未开口,只是以微笑和紧握的双手,传达着那份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感激。
为什么会这样?贝尔和海曼带着问号回国。
在此次访问我国期间,他们最感欣慰的瞬间,莫过于在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中,意外发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合影:那正是他们31年前与毛主席的珍贵影像!那一刻,惊喜与兴奋之情油然而生。贝尔四十年时光流转,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他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记载:
在那个酷热的七月午后,我偶然瞥见了墙上那张泛黄的放大照片,岁月的痕迹让它略显斑驳,但其中的笑容和情感依旧鲜明。我急忙跑出去,迫不及待地招呼我们的二战退伍老兵及其家属们赶紧过来看。他们的脸上顿时流露出惊讶和喜悦。我好奇地询问讲解员:“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挂上的?”讲解员的回答是:“1958年。”那正是冷战的高峰期啊!这让许多美国人难以置信:即便在那样的年代,中国人民对与我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依然如此珍视。
在向同伴们满怀激情地讲述起当年与毛泽东共进晚餐的点点滴滴之后,贝尔他还向我们传达:“毛在讲话时,对我们的未来,对所有青年的未来,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与乐观。他坚信,青年将在塑造世界的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一刻,毛提醒我们,太阳即将西沉,若想留下影像,便需把握住这美好的光景,前往花园中拍照。我们便照此行动,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永久定格。我一直将这张照片视为无上的珍宝,而令我惊讶的是,中国人对它的珍视程度也丝毫不逊色!”
“直到今天,”贝尔续写如下,“我依旧能深刻感受到,在那次旅行中,成百只伸向我的手,紧握时传递出的温暖与力量。每当提及我们1945年与毛的历史性会面,人们便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充满热情的双手,与我们紧紧相拥。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教室、饭店或托儿所,我们无数次被邀请分享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个噩耗传到大洋彼岸,在我们这些美国朋友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纷纷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悼念文章。海曼的一篇还曾被《人民日报》译成中文发表,题目是《一等兵怀念毛主席》。他开门见山就说:
听闻毛泽东离世的消息,一个路人的偶然提及让我心头一震,仿佛有一股力量在我体内凝固。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尽管我是一位在纽约出生、成长并定居的美国人,毛泽东却以某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这是何种原因?或许学者会称他是诗人、史学家或是革命家。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充满热情、沉着冷静且极其亲切的人,他的风度让人瞬间放松自在。他对周围人的亲近感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与工人、厨师、服务员乃至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充满了温馨的友情,我并未在他身上察觉到一丝高傲的架子。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终于领悟到了为何在听闻毛主席离世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深处会感受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凝固。毛泽东,他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舵手,是他引领着我们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体人民的集体觉醒与齐心协力。那些我在1944至1945年间所熟知的中国人,他们正是毛主席的弟子。而如今,亲眼目睹的新中国成立,也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靠谱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